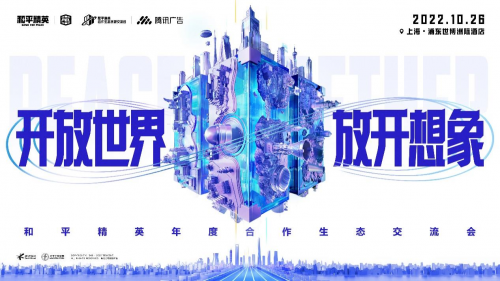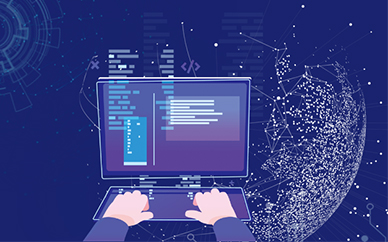《书目答问》在今天一般被视为目录学著作,其学术文化价值早已获得公认,自不待言。但是,《书目答问》的编撰与晚清书院教育关系密切,如果忽视或脱离书院教育的背景来谈《书目答问》,往往会出现一些认识上的偏差,甚至是学术上的盲点。本文尝试将《书目答问》还原到当时书院教育的脉络中,重新审视其编撰意图,并综合多种书院相关的材料,对长期聚讼不止的《书目答问》作者公案,提出新的解释。张之洞喜欢办学,生平最得意者,“任湖北学政时,捐廉创立‘经心书院’;任四川学政时,与督部吴勤忠公商,筹立‘尊经书院’。皆选调高材生肄业其中,亲定课程,成就人才不可胜计。任晋抚时,创立‘令德堂’,皆课通经学古之学,不习时文”。可见,创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,是张之洞办学的得意之笔。同治十二年(1873)六月,张之洞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,同年十月,奉旨简放四川学政。据川督赵尔巽《已故大学士兴学育材成效卓著,请宣付史馆折》引用川籍绅士伍肇龄等人的评价,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的功绩可归纳为五条:会商总督、延聘名儒、手订章程、扩大庋藏、开设书局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其中,第三条“手订章程”是指“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,皆该大学士手订,条教精密,略如诂经精舍、学海堂规模。”此处有三个要点值得引起注意:
第一,所谓“院内章程”,今已不得见,所存者仅《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》一篇,相当于学规,张之洞《致谭叔裕》已明言:“章程有稿存案,《书院记》即学规。”《尊经书院记》既是学规,同时也是《輶轩语》和《书目答问》的精华本,因为张之洞在《记》中明言:“使者所撰《輶轩语》《书目答问》言之矣。犹恐其繁,更约言之。”
第二,“读书治经之法”,即张之洞为尊经书院的院生们编写的《輶轩语》和《书目答问》。光绪二年(1876)尊经书院所刻的《书目答问》原本就是与《輶轩语》合刊的,说明这两本书在内容上存在某种关联,否则没必要合在一起。《輶轩语》,“本名《发落语》,或病其质,因取扬子云书《輶轩使者绝代语》释之,义谓与蜀使者有合,命曰《輶轩语》”。由此可知,“輶轩语”乃“发落语”的雅号。“发落”原是处理、处置的意思,对于学政而言,“发落”却是一种特定的职务,指对生员进行考核、录取、奖惩等工作。《钦定学政全书》卷十九对“发落”有详细的规定。按规定,考试发榜以后,生员必须亲自到场接受赏罚,此时,学政要对各等生员进行一番申斥、告诫或劝勉,这些话就称为“发落语”。《輶轩语》就是这样的“发落语”,是张之洞以学政的身份履行自己“发落”的职责,无论其形式上寓规劝于说教也好,客观上对后人读书治学具有启发作用也好,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出发点。
同理,《书目答问》与《輶轩语》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,张之洞在“略例”中开宗明义:“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,非是著述。”光绪二年(1876)闰五月,张之洞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谈到《书目答问》的编撰意图:
弟在此刊《书目》,以示生童,意在开扩见闻,一、指示门径,二、分别良楛,三、其去取分类,及偶加记注,颇有深意,非仅止开一书单也。更有深意,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,而重刻或访刻之。
关于张之洞欲劝勉士绅刊刻书籍的“深意”,有学者已指出过,此不赘述。这里仅想指出一点,采访遗书,以广见闻,劝勉翻刻,以广流传,本身也是学政职责范围内的事情。《钦定学政全书》卷三《采访遗书》、卷四《颁发书籍》对学政访书、刻书有明确的规定。例如,乾隆六年(1741)上谕:“近世以来,著述日繁。如元、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,研究六经、阐明性理、潜心正学、醇粹无疵者,当不乏人。虽业在名山,未登天府,著直省督、抚、学政留心采访,不拘刊本、抄本,随时进呈。”又如,乾隆三十九年(1774)上谕:“应于《提要》之外,另刊《简明书目》一编,只载某书若干卷,注某朝某人撰,则篇目不烦,而检查较易。俾学者由《书目》而寻《提要》,由《提要》而得《全书》。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,用彰我朝文治之盛。”由此可知,《书目答问》的编撰,实际上是张之洞按照上谕的要求,贯彻和推进清朝的文治教化,它与今天研究编目方法和规律的目录学在出发点上并不完全一致。
第三,张之洞手订教条(包括《尊经书院记》《輶轩语》《书目答问》),“略如诂经精舍、学海堂规模”。这是讲张之洞在学政任上的所作所为,皆以清朝名臣阮元为楷模,处处效法他的政绩。例如,阮元创建诂经精舍、学海堂,张就仿效创建尊经书院;阮元撰《诂经精舍记》当作学规,张也撰《尊经书院记》当作学规;甚至有人认为《輶轩语》和《书目答问》也是仿效阮元任山东学政时刊刻的《经籍举要》。以上这些都说明张之洞的兴学举措大体出于为政、为官的需要,并不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。
综上所述,《书目答问》本质上是清代官师同课、政(治)教(育)合一的书院教育制度的产物,它和《輶轩语》的编撰意图一样,都是遵奉上谕行使学政应尽的职责,而且这些职责都有前辈名臣的先例可循,并非张之洞的创举。
关于《书目答问》的著作权纠纷,近百年来聚讼纷纭,几乎成为学界的一桩世纪疑案。陈垣、柴德赓、朱维铮等学术名家均对此书的作者问题进行过辨析,但终究莫衷一是。事实上,前人对《书目答问》著作权的考证,存在一个较大的误区,即纠缠于此书作者到底是谁。其实,无论考证出此书是张之洞自编的,还是出自缪荃孙或其他人之手,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最关键的问题是不管谁编撰了《书目答问》,在当时的条件下,必有参考的蓝本。找到这个蓝本,著作权的纷争就能迎刃而解。
让我们回到《书目答问》的诞生地———四川省城尊经书院,它位于僻处西南一隅的四川成都,远离当时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,而且书院刚刚草创,书籍资料匮乏。按张之洞自己的说法:“京师藏书,未在行箧,蜀中无从借书。”在这样的情况下,要编撰一份分门别类开列了约2500种图书及其版本的长长的书单,谈何容易?更何况“此编所录,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进十之三四。四库虽有其书,而校本、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”,在无从借书的蜀中,这如何能办到?所以,唯有求助于“前辈通人考求定者”。
据苏州图书馆藏无名氏《莫邵亭手钞知见书目》抄本封面题识:
此目录乃钞莫邵亭先生手钞本。标记半用邵位西所见经籍笔记,又汪铁樵朱笔于邵本勘注,并增入邵亭所见所知。惜仅有经史而无子集,倘他日补钞完全,亦一快事。所见张香涛学使新撰《书目答问》,即以此书为蓝本。
其实关于《书目答问》以莫友芝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为蓝本一事,当年尊经书院的院生就有知道底细者。例如,廖平、杨锐是第一批入尊经书院肄业的学生,而且成绩优异,深得张之洞器重,名列“尊经五少年”。吴虞《爱智庐随笔》记录了与廖平的一次谈话,其中就提到:“《书目答问》为莫子偲底本,或言谬(缪)小珊也。”此处的“或言”指杨锐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书目答问”条曰:“华阳杨叔翘(峤)锐曰:此目出江阴缪小山荃荪之手,实非之洞之书。”
所谓“莫子偲底本”就是莫友芝《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(以下简称《郘亭书目》)的钞本。由于此书刊行于宣统元年(1909),距莫友芝去世已近四十年,其间仅有钞本流传。据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,莫友芝与张之洞初识于咸丰九年(1859),当时二人同在京师,私交甚笃。该年岁末,莫友芝离京,张之洞有《送莫子偲游赵州赴陈刺史钟祥之招》一首送别。同治六年(1867)十月,莫与张偕行至无锡,作竟日之谈,离别时互有馈赠。同治八年(1869)二月莫对张又有书信馈赠。是年十一月,二人有书信往来。《郘亭书目》的钞本极有可能是张之洞在与莫友芝交往中得到的。而且,莫友芝比张之洞年长26岁,与《书目答问略例》中提到的那位“前辈通人”吻合。
为证明《书目答问》以《郘亭书目》为蓝本,下面从《书目答问》中抽取史部载记类,与《郘亭书目》作一对比:
从列表可以看出,以上十三种书,《郘亭书目》与《书目答问》互异之处有五(皆以黑体字标出)。其中,《西夏书事》一种,《书目答问》未标明卷数,说明作者并未见过此书,只是有所耳闻。而且,当时尊经书院的师生也没见过这本书。例如,光绪五年八月七日,王闿运就因此书而与尊经院生有过一场争论:“谢生树楠呈友松《西夏事略》,廖季平云张孝达见一种,杨生鳣塘云或即此书也。孝达注云‘时人作’,非前代成书明矣。”可见,由于《书目答问》语焉不详,竟有尊经院生将开县陈昆的《西夏事略》误认为是吴广成的《西夏书事》。《江南野史》一种,《郘亭书目》所列四库依抄本、淡生堂馀苑本非普通读书人所能见,故《书目答问》易之以常见的续百川本、函海本。马令《南唐书》一种,《书目答问》仅多添“江西翻本恶”一句,为《郘亭书目》所无,恐怕是版本太劣,莫友芝没有著录。因此,《书目答问》比《郘亭书目》多列出版本的仅有《邺中记》《九国志》两种。
假如上述列表尚不足以证明《郘亭书目》与《书目答问》之间的关系,那么,试再举一例。陈垣先生《艺风年谱和书目和问》引到光绪九年(1883)陆心源致潘祖荫的信札。
张中丞所刊《书目答问》,世颇风行。如《考古续图》,流传绝少,惟天禄琳琅及叶氏平安馆有其书,《答问》列之通行;朱石君《知足斋文集》乃散行,而列之骈体;毛岳生、吴仲伦、刘孟涂、管异之,称姚门四杰,而独遗毛氏,亦百密之一疏也。
陆心源信上指出的三处硬伤,第一处错得匪夷所思,《郘亭书目》准确著录了此书的作者、卷数和版本,而《书目答问》不仅将罕见的《考古续图》注为通行本,而且将《考古图》作者吕大临误作吕大防,将“《释文》一卷”误作“《释音》五卷”,这些是照抄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都不会犯的错误。何以至此,令人费解。剩下两处硬伤均涉及“修四库时所未有进十之三四”的内容。按张之洞的说法,《书目答问》中有十之三四的书是《四库全书》未著录的。陆心源所举朱珪《知足斋文集》、毛岳生《休复居诗文集》、吴德旋(仲伦)《初月楼文钞》、刘开(孟涂)《刘孟涂集》、管同(异之)《因寄轩文集》这五种书都在《四库全书》未著录之列。由于《郘亭书目》基本上只著录《四库全书》已收书的版本,故没有著录上述五种书。因此,《书目答问》在编撰时就失去了征引的凭据,频频出错。著录朱珪《知足斋文集》,既不知其卷数,又不知集中所收全是散文,没有骈文,列入“国朝骈体文家集”,闹了笑话。著录“国朝桐城派古文家集”时,“姚门四杰”遗漏了毛岳生的《休复居诗文集》。剩下的三杰,除刘开的《刘孟涂集》著录正确外,吴德旋《初月楼文钞》误作《初月楼集》,并且标不出卷数。管同《因寄轩文集》误作《管异之文集》,也标不出卷数。
正是由于《郘亭书目》的上述不足,导致张之洞在编撰《书目答问》时遇到很大麻烦。据缪荃孙回忆,张之洞编《书目答问》时,他随同助理。有一次,张向他提起邵懿辰的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说此书“当时惜未传录,否则出诸箧中,按图索骥,数日事耳,不似如今考及两月,尚未惬心贵当也。”为什么说如果用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按图索骥,不过“数日事耳”,而“如今考及两月,尚未惬心贵当”呢?因为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增入了大量《四库全书》未收的书,可省不少事。而《郘亭书目》没有收这些书,要增补这些“修四库时所未有进十之三四”的内容(近1000种书),要花费很大一番工夫。
尽管《书目答问》对近现代学术影响巨大,但是,它最初在书院教育中所起的作用,似乎还很少有人提及。光绪元年(1875),《书目答问》初刻于尊经书院,这一年尊经书院才刚刚创建,第二年它又与《輶轩语》合刊,成为此后二十多年中尊经院生的必读书。尊经院生刘光谟曾用“通经达史,博学能文,讲求根柢,以期大成”这十六个字概括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。而《书目答问》所显示的正是这种“通博”、“大成”的学术气象。
钱穆说:“每一时代的学者,必有许多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。循此推寻,不仅使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学术上的门径和方法,而且各时代学术的精神、路向和风气之不同,亦可借此窥见。”光绪初年编撰的《书目答问》,从尊经书院开始,一直影响到全国,正是这一时期学术趋向的反映。此后,这种“通博”的趋向在尊经书院更是突破中学的疆界,进而发展到西学领域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尊经书院山长宋育仁从上海等地采购回大批书籍,供书院的院生们研读。四川大学档案馆《四川高等学堂档案》保存了宋育仁当年采购书籍的清单。在这份采购清单中,除为了补足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所列书目外(如《大清一统志》《算学启蒙》等),还购藏了大量西学书籍,门类包括社会科学的历史、经济、法律、政治、文学;自然科学的矿业、冶金、矿物学、工业技术、交通运输、军事、力学、声学、光学、化学、化工、动力工程、数学、地理、天文学、气象学等方方面面。这些西学书籍的涵盖面之广,已远远超出了当初《书目答问》所划定的知识范围。但是,综观尊经书院教育活动的变化发展,我们认为,《书目答问》所奠定的规模和基础,仍然是中西会通的必要前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