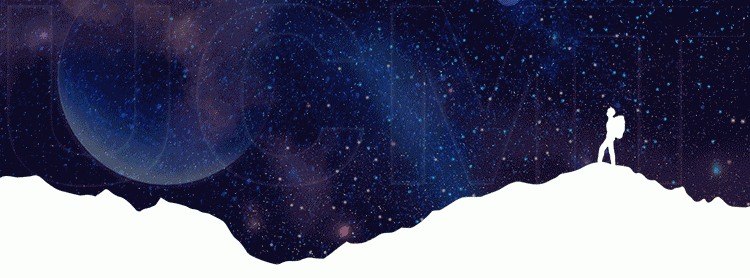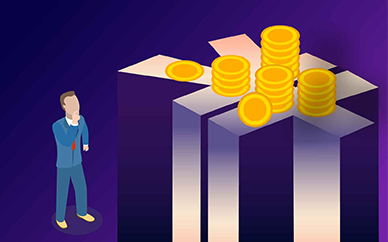#简爱/伯莎
我把故乡掰碎了告诉您,撕开柔软的果肉,溢出西印度群岛丰盈充沛的雨水和常年不息的绿意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黑夜不止掩饰那些晦暗的脏污,它也是弱者能够难得夺取到片刻喘息的庇护所。 黝黑的光线编织成虚假的外衣,把原本的桌椅壁炉都伪装成被冰川切割粉碎的凯恩戈姆山脉,高耸嶙峋得让人不敢逾越。伯莎伸手,恍惚间觉得就连自己的皮肉都快要被阁楼上的死寂和黯淡侵吞腐蚀,从鲜活的肌理一瞬间溶解为虚无。
她以一种徒步跋涉高原的心情试图地从床上下地。冰冷的触感从脚底攀上心房,冻得让伯莎一个激灵,使她的思绪即刻彻底落地生根。这种寒意,是月下窸窸窣窣作响的沙洲,是山谷间夏日不化的冰斗。这里是英国啊。她突然间就顿悟了。
伯莎没能找到她的鞋子。
人们认为疯子不需要鞋子。疯子可以被归类,就像是动物和植物一样分门别类得划归到不同的纲目科中。一些疯子是唐吉坷德般的谐星和笑料,一些是哥特式铜版画上的魔鬼。很不幸,伯莎可能被拨到了后者的行列里,即使她可没有折磨过圣安东尼。罗切斯特也不是圣安东尼那样隶属史诗传奇的人物。总归,疯子是被社会体系化的车轮倾轧在地的遗弃物,与19世纪轰隆鸣响的机器格格不入。
她遗失的鞋子连同外衣淹没在了黑暗里。伯莎在浑水里摸索,只捡回了她的理性。不过那已经足够幸运了。
格雷斯.普尔伏倒在床上,像是地狱门前昏昏欲睡的守门人,却有着三头犬般压抑的鼾声。那像是低沉雷鸣的鼾声如同鞭子抽打着伯莎的脚踝,催促她快点逃离这个野兽洞穴,不然在声响停下来的某刻,也许那看门人又会把她拖进地狱里。
她没有油灯,没有蜡烛,只凭自己身体的记忆越过这一方狭小天地上布置的重峦叠嶂,行走在被截断的悬崖边,绕过猎人隐秘的陷阱,怀揣着生怕发出一点动静的惊惶。深夜黯淡无光,可路始终还在那里。
伯莎终于逃出了阁楼,沿着狭窄的扶梯向下,跌跌撞撞闯进豁然开朗的走廊。
月色开始偷摸溜进她的视,可比那更加明亮的是走廊尽头简爱手里的烛光。伯莎开始奔跑,她与层层叠叠的窗帘擦肩而过,踩过地上碎裂的树影。柔软的地毯是这场隐秘逃亡的从犯,吞咽了所有可能的异响。终于,她近乎扑倒着抓住简爱的手臂,把简手上的睡衣布料搅成了一团。
“上帝,我上一次玩这么刺激的游戏还是在进修道院之前。”伯莎努力克制喘息,急促轻快地对简感慨。简把她拉进了敞开缝隙的房门,目光在门外四处逡巡排查后再度把门关上。
她们盘腿坐在地上。
在这里,没有男人、修女或者家庭教师会勒令她们摆出画上的姿态,而且简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比地毯上更加适合伸展四肢的地方。一只蜡烛的火光不算刺眼,足以摆在正中间照亮她们两人的脸庞。
在万物都沉寂的夜晚,她们可以谈很多除了梦境之外东西。
简跟她描述那些印着油墨的报刊上对于殖民地的争吵,给她阅读流行的胡话诗歌。她不是很能适应那种胡话体,但是《荒诞书》的内容足够新奇,囊括了无由来的梦幻韵律。“它们很像童谣,但又有讽刺文学的意味。”简细细给伯莎讲解。
而伯莎会从报纸上保守派的论调出发,把故乡掰碎了告诉简,撕开柔软的果肉,溢出西印度群岛丰盈充沛的雨水和常年不息的绿意。
“我不认为大多数的黑人都是斯凯特,因为人们无法强求一个没有走过路的人立刻去奔跑。在牙买加,富人零散地分布在宽阔的山腰。从他们的庭院里你可以看见加勒比海的日出日落和每一阵浪潮。而黑人们则蜗居在山脚,那些白人从没有搞清楚一平米里可以挤进多少个黑人……”
山顶的浓雾会滋养出最茁壮的咖啡树,而那种庄园大多属于英国人。富人把那里当做天堂,可他们的天堂是拿金币堆砌的。如果你看见目光可及的海面之间突然横插进一条深蓝,那么那片海域的水底便可能是道深渊。有很多捕鱼人和采珠人就是在那里出事的。但大部分时候,加勒比海的水是凝滞的油画,偶尔会有白色缎带的沙洲淡淡划过一道细线。
那些庞大的巨物无法在陆地生存,可是海里有着轮船尺寸的鲸鱼。谁也不知道海可以容纳多大的生灵。偶尔会有人见到它们搁浅的尸体,霸占了沙滩的一角然后被发现者分割售卖。人们总能绞尽脑汁从海洋里捞出钱来。
还有悬崖下的珊瑚礁石……
夜悄无声息,牙买加的水在桑菲尔德静谧流淌。
【完】